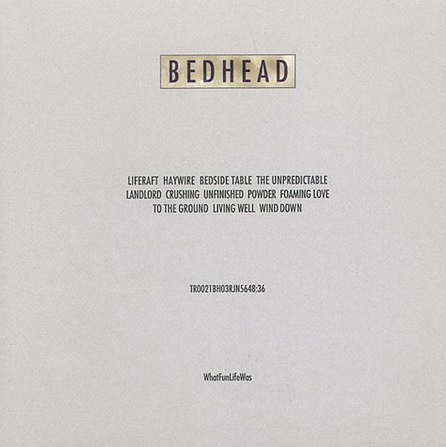說起The Jam和Paul Weller在台灣「搖滾黨徒」間所受到的關注程度,其中的差異還真是不小。比起動輒被冠上「摩德教父」(Modfather)美名,怎麼穿怎麼有型的Paul Weller,The Jam這組讓他在英國樂壇取得一席之地的龐克樂團似乎早被台灣樂迷遺忘。事實上,The Jam在其「出產國」所擁有的影響力仍難以小覷,不僅不時有好野人開出高價盼望重組,今年6月在倫敦的Somerest House更有一檔由Paul Weller的妹妹Nicky Weller協力策劃的展覽— 《The Jam: About the Young Idea》,展出了影片、歌詞手稿、舞台造型等「歷史文物」,顯然英國人對這三位身處七零末、八零初,既迷惘又憤怒的摩德青年還是很有愛的。
「咦,剛剛不是才說The Jam是龐克樂團嗎,怎麼一下又變成摩德青年了,這不科學吧?」沒錯,這種「違和感」就是The Jam獨步樂壇的秘密武器。在服裝造型上,The Jam的三位成員Paul Weller、Bruce Foxton及Rick Buckler從不玩弄Sex Pistols的街頭拼貼風,也不模仿Patti Smiths的蒼白詩人姿態,卻獨辟蹊徑地以筆挺的西裝、服貼的髮型向廣大的年輕勞工階級喊話:嘿,我們是一國的,我知道你們心底的每一個念頭!相同的邏輯也展現在他們的音樂中,像這張融合了放克、流行樂、節奏藍調和龐克的《Sound Affects》,雖然仍被多數樂評視作龐克,卻是不折不扣的「非典型龐克」代表。
如果硬要說Paul Weller代表的是The Jam的靈魂倒也不是不行,畢竟他幾乎包辦了所有的詞曲創作。不過,當專輯開場曲〈Pretty Green〉活跳跳的單音bassline冷不防地躍入耳際時,類似「The Jam不過就是一場Paul Weller的自幹秀」的偏激想法即不攻自破。接著,Paul Weller以略顯沙啞的嗓音唱道:
I've got a pocket full of pretty green
I'm gonna put it in the fruit machine
I'm gonna put it in the juke box
It's gonna play all the records in the hit parade
短短四句話卻將英國勞工階級青年的日常生活作了極深刻的描繪—除了把錢花在點唱機,瘋狂地將所有排行榜上的熱門歌曲聽遍以外,他們什麼也不想/不能做。
有趣的是,當年The Jam所屬的唱片廠牌Polydor原本想將這首帶有批判資本主義意味的〈Pretty Green〉當作首支單曲,卻遭到日後宣稱「自己或許是其所屬世代中,最後一個會思考階級意義的人」的Paul Weller堅決反對,而改以〈Start!〉作為單曲。這首奇異的短歌脫胎自The Beatles的〈Taxman〉,除了擁有幾乎一模一樣的bassline和吉他riff,一句Loves with a passion called hate更精準地捕捉到藏匿在憤怒青年堅強身影背後的溫柔。
若要選出《Sound Affects》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那大概非〈That’s Entertainment〉莫屬了。在這首歌中,Paul Weller拾起了木吉他,化成一位「都市漫遊者」,以若即若離的距離審視著他深愛的同胞,並以詩意的文字將當代英國生活百態記錄下來。不知為何,這使我想起法國小說《鼠疫》中的旅人塔盧,他對城市居民的觀察筆記—根據作者,也是荒謬主義者卡繆(Albert Camus)的說法—「就像倒拿著望遠鏡在看待人事物般」。難道說,將瑣碎的日常光景視為某種娛樂的Paul Weller也是一位荒謬哲學的信徒嗎?
走筆至此,或許有人會說「這麼看來,《Sound Affects》還真是一張飽含批判意識和嚴肅辯證的專輯啊。」其實並不盡然。專輯發行時才22歲的Paul Weller,自然也有「少年保羅的煩惱」,否則他又怎會在〈Monday〉中溫柔傾訴:
Rainclouds came and stole my thunder
Left me barren like a desert
But a sunshine girl like you
It's worth going through
而在〈But I’m Different Now〉中,他彷彿成了唯恐失去愛情的大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愛人賠罪「我已經改頭換面」。激越的龐克少年為愛竟也落得如此「狼狽」,真摯的呼喚配上大剌剌的riff似乎是在提醒我們,愛情才是人們最原始的渴望。
對某些「龐克基本教義信徒」而言,The Jam如此「煽情」的描寫男女意愛,簡直是「不倫不類」,而那些散落在歌曲中的管樂、口哨和迷幻聲響則進一步的坐實了「背叛龐克」的指控。弔詭的是,整張專輯中最使我迷戀的卻是有著雋永旋律的〈Man In The Corner Shop〉,私心認為就連Britpop的全盛時期也沒能產出一首足以與之匹敵的歌曲。這首歌不僅有著一聽上癮的旋律線(我懷疑一切都是『啦啦啦』在搞鬼,這招總是管用),在點出階級矛盾之餘,Paul Weller更以一種宛如宗教人文主義者的姿態堅定地唱道:
Go to church do the people from the area
All shapes and classes sit and pray together
For here they are all one
For God created all men equal
是的,沒有誰應該比誰更高貴,也沒有誰應該比誰更低賤,因為在造物者的眼裏,我們都是一樣的。
整體來說,《Sound Affects》並不屬於那種需要經過一段時間醞釀才能有所體會的專輯;相反的,他裡頭有許多搶耳的橋段,總能使你情不自禁地跟著反覆哼唱。而透過Paul Weller在創作《Sound Affects》時所展露的折衷思維,我們也得以釐清他往後轉變的脈絡,無怪乎這是他最喜愛的The Jam專輯。就這點而言—當然也因為The Jam的重組似乎遙遙無期—《Sound Affects》不但是Paul Weller和The Jam間的最大公約數,也成為無數樂迷最美好的痛。
by Faun